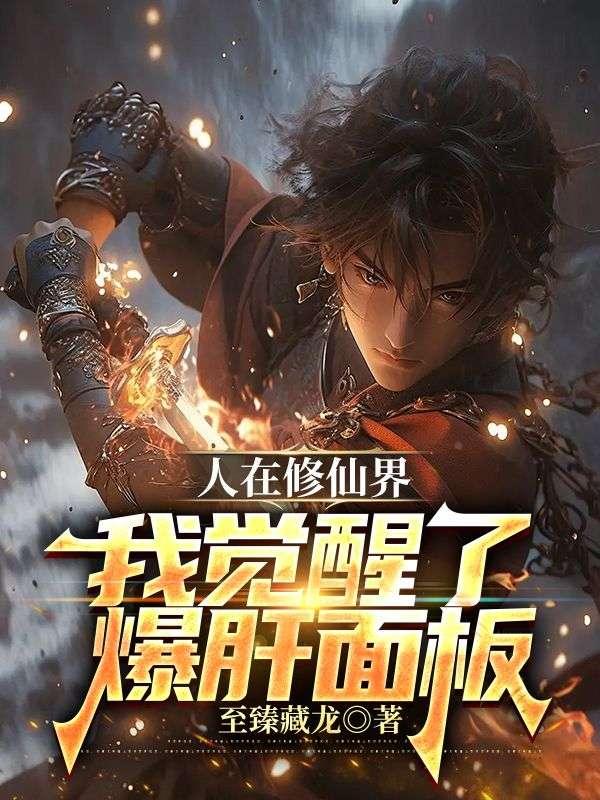天心书盟>女扮男装我拿到登基剧本(科举) > 6070(第29页)
6070(第29页)
他连忙伸手安抚道:“小贺大人莫急,老夫有些话想说,还请小贺大人静心听一听。”
贺云昭眉微挑,疑惑道:“不知老王爷有何指教?”
李煌无奈苦笑一声,“老夫不愿叫小贺大人误会这才特意来拜托叔祖,小贺大人,老夫只想问你一句,你认为此事难道是我儿之错吗?”
“君子论迹不论心,我儿固然险些犯错,但那裴世子嚣张跋扈直接动手,我儿直到如今还躺在床上,凄惨模样你也是见过,无知妇人虽做了手脚,但身上的伤不做假!”
呦呦呦,不愧是老艺术家啊,贺云昭心中赞美一番,面上还是配合露出犹豫神情。
她道:“此事在御前已经了结,不知老王爷您此时再提是?”
李煌瞧着贺云昭神情变化,眼中闪过一抹喜色,他继续用无奈的口气道:“老夫无意为犬子开脱,只是不愿小贺大人过于误会,或许心仍有愤怒之情,但不是冲着你去的。”
他颤颤巍巍起身,抬手就要作揖。
贺云昭面上惶恐上前扶住他,她叹道:“您何必如此,折煞下官了。”
李煌扭头使了一个眼色,小儿子李景捧着盒子上前,年纪不大十三四岁。
他脆生生道:“贺大人莫怪,哥哥他只是一时糊涂,平日里从未有那种神情,也是被人激了才如此作态。”
“哥哥他昨日道自己已经知错了,还叫我带着礼物来赔罪。”
李煌一脸愧疚无奈的看着贺云昭。
他不信这还拿不下贺云昭,此人虽有些智慧,但观其平日里形迹,颇有清高正直之气,他亲来致歉不怕不接受,再加上他特意准备的这份礼物……
贺云昭果然神态微愣,刚要拒绝话却堵在嘴里,她诧异道:“这是我祖父的画作?”
李景展开的盒子中只有一幅画,落款赫然是贺云昭的祖父!
她嘴唇颤颤,眼眸一湿,竟说不出话来,好半晌才接过这盒子。
李煌继续说了一些李晖的愧疚之意,并再次强调李晖被打本就是苦主,他对青年学子的扶持不是为了名声,是他真的那样诚恳去做。
贺云昭忍住眼眸湿意,道:“下官知道,安王殿下素来喜爱诗词歌赋,曾听几位年轻学子说过此事。”
成了!李煌心中得意,他继续安抚几句。
“是非对错,你心中也应当明白,晖儿受罪已经得到了他的惩罚。”
他甚至还做戏做到底,回忆了一下贺老爷子的昔年事迹。
贺云昭神色认真的听着……
……
“三爷。”
“嗯。”
贺云昭从襄王府出来上了马车,她立刻呼出一口气,将盒子收好。
她拍拍自己的胸口,心里夸自己一句,演的真棒!
安王始终是一个定时炸弹,必须要处理,但问题在于如何处理。
她有想过放出消息,将安王伤势做假与他任由母亲顶罪之事全部捅出去,如此一安王名声就毁了大半,可对安王府来说还达不到伤筋动骨的程度。
李晖若是破罐子破摔的对她动手可就难搞了,只有千日做贼的哪有千日防贼的。
她将事在心里重新过了一遍,抓住了其中一点,那就是在安王府与宗室看来李晖其实很委屈的,不算其中动的手脚,本质上裴泽渊就是动手了。
有没有一种可能,能让此事为她所用?
贺云昭回府后,并未去书房静静思考,反而是去了二姐的院子。
贺锦墨正同后巷叔父家的堂妹等姐妹一同缝制各色成婚用的物件。
女子成婚有不少需要自己准备的东西,贺锦墨的嫁衣是请了绣娘专门到府里来制的。
嫁衣包含了上衣、下裙、霞披,金银线、孔雀羽线制成的云锦用了足足五匹,再加上李旷乃是宗室子弟,按照规制还有许多图案要绣上去。
贺锦墨最初打算自己来缝制嫁衣,只是做了四五日,她累的脸色发苦。
人都说女子缝嫁衣时欢喜羞涩,但她欢喜了不到两刻钟累的便有些气,甚至都不想嫁人了。
可女子嫁人皆是如此,她累得很也不好意思说,说来便显得她极不懂事,只好把累往心里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