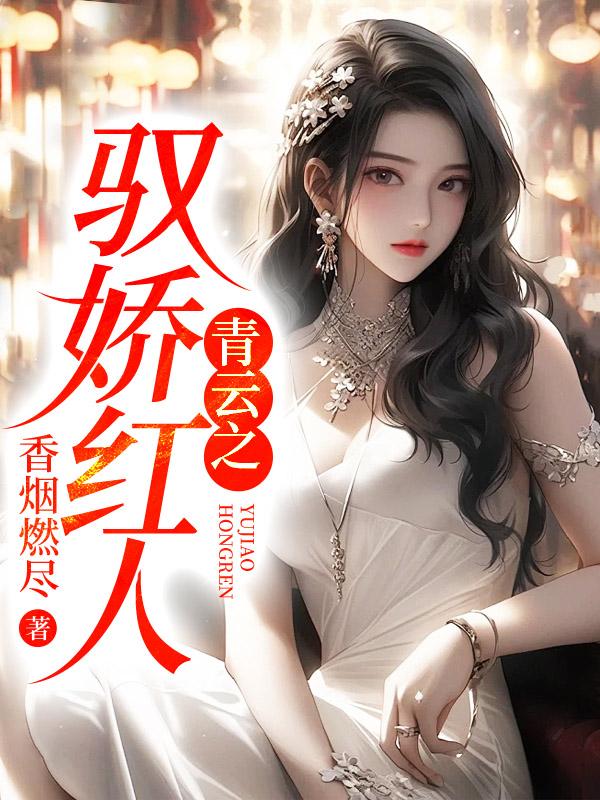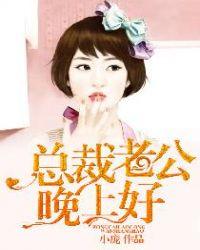天心书盟>乱世春秋 > 第10章 后庭桃花笺(第8页)
第10章 后庭桃花笺(第8页)
“拿着!”她把围巾塞进慕廉手里,“外头天冷,别冻着。”
慕廉接围巾的手抖了抖——这灰蓝毛线是去年冬典当嫁妆换的。他记得许婶就着油灯织围巾时,总嘀咕败家玩意儿配这色正好。
“婶子…”
少年膝盖砸在青砖上的闷响,惊飞梁间燕,这些年…喉头突然梗住,像吞了块烧红的炭。
慕廉鼻头发酸,双膝跪地,郑重叩了第三个头:“谢婶子这些年照顾,教我做人,教我为人处世”
此头,谢成人之道。
“起开!少学戏文里酸秀才做派!”却突然噎住,扑过去把他搂进怀里,哭得更厉害,嘴里还骂骂咧咧:“白眼狼!有了本事就不认娘了!”
泉涸,鱼相与处于陆,腌芥菜的酸香,混着新米炊烟。
许婶粗粝的指节刮过他手背,七年前那个雪夜忽在眼前晃荡。
他因划破许叔的蓑衣,躲在村祠不敢归家,也是这般寒彻骨髓的清晨,许婶拎着烧火棍寻来,将他冻成萝卜的手指塞进怀里捂着。
那夜她没骂人,许婶不识字,只说:“犯错如蓑衣,破洞要自己补。”
农妇的泪珠子砸在他后颈,烫得朝阳剑在鞘中铮鸣。慕廉嗅着她襟口沾染的艾草香,这农妇骂人时喷出的吐沫星子,只是坦护所爱之人。
“走吧,男子汉大丈夫,总不能一辈子窝在家里。你婶子嘴硬心软,别放心上。外头路远,记得常写信回来报个平安。”许叔吐了个烟圈,在一旁笑着劝。
村口老槐下,许婶往包袱里塞进最后一包炒黄豆:“敢弄丢围巾,仔细你的皮!”她转身走得比风还急,却漏了声呜咽在霜地里。
“小兔崽子!”五十步外突然炸开吼声,“要是混成汴河边上那些穿绸戴银的王八羔子——”枯枝咔嚓折断,“就甭认我这个养娘!”
慕廉摸着颈间粗粝的毛线,突然笑出泪来。晨雾里传来许叔烟袋锅敲击槐树干的声响,三轻两重,正是当年走镖的‘一路平安’暗号。
……
慕廉背影消失在雪路尽头,天地间归于寂静。
屋内,轮椅上的妇人静静地坐着,阖目如眠。她的脸上没有悲喜,鬓间的青玉小剑簪在晨光下泛着幽幽的光。
不知过了多久,她缓缓睁开双眼,垂首嗅了嗅襟前艾草香囊——针脚是照着十六年前某件婴孩肚兜绣的,彼时绣绷上还沾着产房未拭净的血渍。
“痴念已了。”
她望向空无一人的门口,晨光穿透她逐渐透明的指尖,唇角浮现出极淡极淡的微笑。
她这一生,孤苦流离,飘零如浮萍,曾经的执念与遗憾,早在孩子成长、亲情圆满的那一刻,化作了一缕轻烟。
随即,像雪落无声一般,她的身影渐渐淡去,消融在天地之间,只余一缕温暖的清香,飘散在残雪未化的庭院。
——
雪后初霁,日晷铜针挪至隅中位时,玄衣广袖扫过阶前残雪,女子面覆青铜面具。
她踏进院落,驻足片刻,目光落在轮椅旁残留的那支青玉小剑簪上。
喀嚓——
鞋底碾着残雪,玄衣女子每踏一步,那些被妥帖收藏的往事,此刻正随她步履化作雪泥:
三岁孩童滚烫的额紧贴她小腹剑疤,泪痕渗进当年剖腹取子的刀口;五岁孩童藏在妆奁底的麦芽糖,融化了用来梳妆的朱砂;七岁孩童开蒙那日,便是用簪子蘸着灶灰,在黄表纸上教他写第一个‘人’字……
“孽障。”
她弯腰拾起簪子,指腹摩挲,神情不悲不喜。
喀嚓、喀嚓——
雪地浮现的剑痕,像被揉碎的桃花笺,袖袍翻卷如墨云压城,青玉簪尖挑破指尖。
血珠坠地刹那,庭院忽现两重幻影:东厢房内女子正为少年缝补冬衣,西窗下玄衣女子却将匕首抵在婴孩眉心。
两道身影随飘雪渐融,唯余满地冰晶映出千面残像。
雪地上空余两行脚印。向东那串深陷如刻碑,向西那串浅淡如鹤羽,中间隔着三片未化的残雪,正拼成模糊的慕字半边。